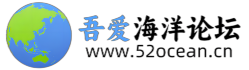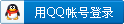这里展示的一个个故事,概略地描述了作者从1955年投身海洋,到2008年的50余年间,从事海洋教育、海洋调查工作半个世纪历程,内容涉及海洋科学的诸多方面。 故事以时间顺序展现了一些知识性、可读性较强的事例奉献给读者,进一步诠释物理海洋学奠基人-赫崇本先生那深邃的哲学思想:“欲做海洋事,先做海洋人”的丰富内涵,同时解读“水是灵动多变,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辩证观点,让后来从事海洋调查研究的年轻学者得到一些启发,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和损失。 海洋既能让人充满想象的空间,也是充满各种风险的战场;它可以使人变得勇敢,也可以使人变得怯懦。笔者希望年轻的和未来的海洋事业继承人,能对祖国富强怀有巨大的责任感,成为大海中翱翔的海燕! 科学的海洋调查,是通向海洋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新的调查手段的出现,能够推动海洋科学向纵深发展。海洋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民族独立的精神,从而对人类满怀庄严的使命感。 笔者力图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知识告诉读者,既有科学性,又不失趣味性,其中还有不少东西可供细细品读。笔者相信,开卷有益,学取精华做刀枪,知识就是力量。 七、鏖战黄河口 [49]三个蚊子一盘菜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辞青、甘,跨宁、内,奔腾于晋、陕之间,破“龙门”而出,横穿华北平原,急奔渤海之滨,矢志入海,九曲而不悔。以她那母亲般甘美乳汁,哺育着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繁茂了中华民族。 黄河中游河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支流带入大量泥沙,“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九曲黄河万里沙”,其总输沙量每年可达11亿吨。因此,在入海口的东营市附近,淤积了一马平川的黄河三角洲,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并且还以每年2-3平方公里的速度向海中扩展。 如果把每年的来沙量平铺在黄河三角洲的土地上,可使地面增高20厘米;如果把这些泥沙堆成长堤,3年就可造出一条万里长城!泥沙沉底,使河床不断加高,下游河道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河”。在开封,河底与城里烈士纪念碑的塔尖一样高;在济南,与老城墙顶一样齐。 很难想象,万一鼠洞蚁穴为患,溃孔而决长堤,河水从几十米高处瀑流而下,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河床抬高,河水入海就不流畅,因此,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每隔七八年河水就要改道一次,以自然或人为方式降低河床高度。 这里的天气多数是晴空万里,降雨量远小于蒸发量,因此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地严重碱化。树木不长,即使栽在特殊设置的高台上由人工浇灌,在碱风、碱土的影响下,仍然生长缓慢,甚至枯萎成柴,只有那最不怕盐碱的盐蒿和一些野生的杂草生长。 夏天,走在深可齐腰的盐蒿和杂草中,一股淡淡的香草味弥漫在空气里,其中似乎还能感觉到咸咸的味道。被人们脚步惊扰起来的蚱蜢和草虫,淅淅梭梭地在身前身后跳动。那令人讨厌的蚊子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你,对你身体所有裸露的部分,例如,面孔、脖子、手面和小腿叮咬下去,不消片刻,被叮咬部分就布满红疙瘩,痒入心肺。 据说,咬人是雌蚊,喝过人血,产卵会多十倍,不过寿命只有一天,咬人只有一次。我认为应该像芬兰人那样,在旅游指南中写下:“这个季节对你不离不弃的只有蚊子!”可惜,我们现在的旅游指南是千篇一律地说好不说坏,报喜不报忧。 草原深处,有时会突然出现一泓碧蓝的池水,水质清澈,但是,却看不到一条游动的鱼。只有生养在其中的水草,随着流势轻轻摆动。到了晚上,断霞横空,月影在水,一片空明。据说,这是风暴引发的潮水登陆之后遗留下来的,再经过蒸发浓缩,其中盐度高达千分之四十以上,水质咸苦,连海鱼都难以生存。 但是,这里却是蚊子孳生地。在咸水中繁殖的蚊子,比淡水中孳生的蚊子要厉害10倍!个头大,传说三个蚊子一盘菜,如果画家搞一个蚊子特写,大眼睛、大嘴巴、大翅膀,整天对人虎视眈眈,一定非常有趣。 黄河滩上的蚊子多得不可胜数。石油工人李双全想统计一下野外石油工人住地蚊子的密度,他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把10多平方米的工棚空一晚,天黑敞开门窗,挂个照明灯,第二天一早把门窗关闭,喷了灭蚊子的敌敌畏,然后进去扫死蚊子,竟扫出满满一簸箕,差不多有一斤。 还有附近村里农户家的一头牛病了,晚上灌了药,第二天一看它死了,身上覆盖了大约几万只蚊子,鼓着满肚子牛血,飞不动了。原来这牛有病,无力甩头摆尾,驱赶蚊子,生生被蚊子咬死了。 想到这里,我从心眼里佩服,日夜奋战在这里的石油工人。他们是一批朴实无华的劳动者,默默做着坚忍不拔的奉献。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成功并不仅仅属于那些明星,而是属于所有勤奋努力的人。 冬天,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黄土遍地,衰草连天。云朵又多又大又平整,随着风的吹刮,在蓝天上列队飞过,那投在地上的阴影变得忽明忽暗,人好像走在梦里。 水流沙漫,巨量泥沙每年从海中堆起大片陆地,在这惜土如金的今天,也是一批不小的财富;入海的淡水和夹杂于其中的营养物质,是渤海各种鱼类,特别是对虾赖以生存和繁殖的基本条件。 1961年,几十万以石油工人为骨干的建设大军云集在这里,各种石油井架像雨后春笋般耸立。几年之间,“胜利油田”的名字,响遍华夏大地。一座新兴城市---东营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也在黄河三角洲荒原上冉冉升起。胜利油田要发展,东营市要建设,黄河几年一改道的现象必须得到控制。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稳定黄河流路的办法,同时在黄河三角洲边缘找寻一个合适地点建造黄河大港,以适应日益增加的运输需要。 从1983年农历正月第一脚踏上黄河三角洲开始,直到1986年黄河海港(后改称“东营港”)从莽莽荒原上拔地而起,我们在河口与大海上曾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尝尽艰辛,终于摸到了一些规律。 [50]初访黄河三角洲 1983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我们一行4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坐着越野车行驶在距家千里之外的黄河三角洲的荒原之上,安排并布置即将开始的黄河口各项建港前的海洋调查工作。 黄河三角洲有着缓慢而优美的起伏,像是放大了的微微动荡的海浪,眼睛可以望到无穷远处。苍天如一座硕大无朋的穹顶,以浑圆的弧度覆盖着这片土地。而我这小小身体,就是这片天地的圆心。如果我把身体做360度旋转,那这里莽莽荒原也绕着我转一圈。无论我走多远,我始终是圆心的中间点。 那个时候,草原上根本没有人工铺就的路:不管是石子路还是柏油路,只有石油工人运输的汽车在草地上压出来的土路,坑坑洼洼,被无数车辙扭曲了的路。当时陪同我们的胜利油田指挥部的同事曾开玩笑地说,这里没有路,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你想到哪里去,都能走得通。汽车在高低起伏的原野上行驶,摇晃得骨头都要散了架。 汽车经过4个小时颠簸之后,我们来到由众多刺槐掩映着的平房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军马场。早在60年代,因为这片土地上芦苇长势茂密,济南部队在这里建了养马场,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匹军马在这里放养。现在这个使命可能已经结束,因为我前后左右寻找一圈,只在棚子里看见一匹枣红马,可能是工人作为临时代步之用。 据工人介绍,这里养马场历史悠久,早在唐朝李世民时期,就养过军马。对此,我半信半疑。因为黄河从1855年才从苏北改道入渤海,距今不过百载,而李世民治下时间距今已有1350多年,那时这里应该是“浩浩乎白水”,是海马而不是军马遨游的自由王国! 我们把晃散的骨架刚刚对接起来,就告别热情接待者的絮语,继续往“五号桩”进发。五号桩,是最早的一口靠近海边的5号钻井平台,尽管,后来井架早已撤离,但是“五号桩”已经成为至今使用的地名。那里将是未来黄河大港的选址之一。 到了“五号桩”,石油工人已经撤走,只留下油迹斑斑的的高台。我们爬上平台向东瞭望,只见滚滚黄水夹裹着密集的冰块,挤撞着向南流去。 冰块大者有20多平方米,小冰块也有几个平方米。不少冰块在浪的撮合下,碰撞、堆积成小丘,上面站立着几只海鸥,在凛冽的寒风中无精打采缩着脖子,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流到岸边的冰块不断堆积起来,聚成一道道水丘,千姿百态,形状各异。我跑过去捞起一块冰凌舐舐,凉冰冰的,淡中略带咸味。 看到这里,我心中暗下决心,夏秋季节必须结束各项海上调查,冬天的流冰是我们招惹不起的。“五号桩”南边有一个深入陆地的小湾,将是未来5条租用来作为临时调查船(小渔船)的屯聚之地。 [51]穿越黄河口 黄河入海有南、中、北三个口子。南口最大,中口次之,北口最小。滚滚黄河水打着漩涡从三个口子夺关而过,气势十分磅礴,使船不敢贸然靠近。 河水流出口子后,速度渐缓下来,盘踞在口外东西宽约五公里,南北长约二十公里范围内,随潮流而动,状如龙头“金冠”,赫赫然,气象万千。再向外,水一下子变得湛蓝,黄蓝交界处便是河口锋面,这里流向很复杂,盐度相差也极大:蓝水盐度可达千分之二十七,黄水中盐度只有千分之几。 不少作业的渔民在淡水用完以后,到这里取上黄水,沉淀后饮用。有几次,我们也不得不靠这种水维持生活。 历史上平均每隔8年,黄河就要改道一次。现在的河口,是1976年从五号桩北部迁移过来的。按照常规,显然气数已尽,又到“大改道”一年。但是,黄河三角洲今非昔比,以石油工人为主体的新村镇不断涌现,无论从哪里改道,都是一场灾难。 由于黄河泥沙量高,进入海中的口门处淤积快,形成面积很大的拦门沙,水深最浅只有半米,拦门沙外面是一个“河口悬崖”,水深一下可以增加到4-5米,深度变化十分剧烈。 去年冬天,山东海洋学院(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的“东方红”号调查船开到这里,海图上标明深度为15米,可是吃水仅5米的船体却触了底。幸亏倒车快,才从泥滩上滑了出来。1982年6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现在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局)的一艘调查船,也在这里搁浅十几个小时。因此,许多大船视为畏途,到此不敢轻越“雷池”一步。 1983年9月17日早晨5时,我们4条船从羊角沟起航了。顺着那弯弯曲曲的航道,犁开一道道浅浅波纹,行驶了2个多小时,才到达开阔水域。两岸芦苇已经远远落到后面,船转向北,直奔黄河口而去。 中午12时,水色越来越黄,最后完全变成泥浆,黄浪翻滚,水汽迷茫。由于流入的河水与外海涨潮水相向而行,最后相遇相撞,形成上下跳跃的激浪。其声如疾风骤雨,其外观如沸汤。我们船只顿时失去自控能力,急剧“摇头晃脑”。而那1吨半的潜水船,竟像一片无助的叶片,随波逐流而去。捆绑在甲板上的油桶,刚刚从羊角沟装满柴油,在浪的颠簸下,捆绳松脱,油桶竟滚下海去了。 尽管我们这些老调查队员身经百战,可是遇到这种跳跃的海浪,也会产生头痛、心虚、反胃的不适。我紧急下令船只迅速离开河口,去追赶失去控制的潜水船。经过半个多小时搏斗,才脱离激流险滩,来到比较安全的水域。 在这里调查,最怕“无人舟自横”。船一旦横流便急剧摇摆,有好几次把人甩到水里。第一次没有准备,人被冲出去好远,多亏邻船相救,才化险为夷;后来人们身上都系好保险带,人又被甩下几次,幸好自己都爬了回来。不过当脚触到那滑腻腻、软绵绵的淤泥时,身子直下陷,使人容易产生一种坠入“地狱”的恐怖。 远离河口又是一番天地:水中游动着密密麻麻的毛虾,不时从水中跃出,瞬间又落回海面,随之发出急骤的“沙沙”声,像夏季捶打高梁叶子的暴雨声音。 看到周围樯帆林立,穿梭拖网,我们也不禁手痒。叫船员在船边临时架起一个网兜,放入水中,一会儿就捞上一兜绿玉般的毛虾。船尾大锅支起来,放入木头点着火,很快一碗碗冒着蒸汽的毛虾,就到了每人手中,味道鲜美,是非常好的食材。 黄河口北部是对虾集结之地。我们船经过时,成群对虾悠然而去。间或有4~5只对虾受惊跃出水面,张须振戟,晶莹透亮,像翡翠那样好看。 [52]海滩惊魂 9月18日傍晚,来到“五号桩”。这时,黄昏的落日犹如一个红彤彤火球悬挂西边,染红地平线。不久,令人不安的黄昏如期而至,夕阳偃旗息鼓,几抹被遗弃的晚霞毫无章法地涂抹在西边天际。岸上用于定位的石油井架渐渐融入夜色,平日熟悉的定位目标怎么也找不到。 在黄河三角洲调查最大困难是,岸上无明显目标可供定位。上一个世纪时还没有GPS这种方便而又精确的定位仪器,只能用手拉的六分仪来找寻船只位置。六分仪定位要预先知道岸边3个确定点坐标,然后量取两两确定点之间角度,借助三杆分度计,求得船只位置。 而黄河三角洲是由黄河泥沙填起来的,海退陆出,除去村庄,只有石油井架高出陆地10米以上。在远远的海上看来,也只是远方地平线处一根灰色的“铁棒”。而石油井架是“千架一面”,没有彼此区分的特征。 看着标有井架的海图,心中了然,可是一到海上我们就糊涂:在千篇一律的灰色背景上,所有井架都是扑朔迷离,无法确定我们所需要的桩址。 在打出油之后,井架拆走,即使临时海图上标出某某井架的名字和位置,但到那里一看,却是架去人空,只有一块100多平方米的油渍斑斑黄土高台遗留在那里,或者只有一架灰色的“磕头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磕头抽油”。井台下面曾经居住过钻井工人的集装箱式活动板房,也被拖走,齐腰深的茅草,掩盖了所有人的足迹。 所以,出海之前要到胜利油田指挥部去讨最新的井架坐标,并一一画在海图上。船只一到了海上,我就要站在矮矮的临水甲板上,对照海图查看新的井架,用前方交汇的方法,量出角度,确定船只行走的路线和位置。 为了迅速搞清岸边的一个定位目标,我们7人要乘上一条装有马达的大舢板,在朦胧的月色下向岸边开去。周围万籁俱寂,小船激起的浪花发出轻轻喧哗,不知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船舷,我又想起了那条死鲸和渔民含糊的回答。 尽管我已逾“不惑之年”,然而心中仍有一点忐忑不安的感觉。懊悔不听渔民的劝阻,连晚饭也没吃,便摸到这陌生的地方来。事情偏又凑巧,刚来时还是星斗满天,这会儿居然乌云密布,把一弯银月遮盖得严严实实。船上没有罗经,连方向也搞不清了,我们只好摸索向前。 不久,舢板上的马达又坏了,黑灯瞎火一时难以修复,试一试水,不深,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前进。我扫了一下黝黑的海面,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大概我们趟水的声音惊动了岸边沉睡的海鸥:“哇!哇!”地叫着飞向天空,但这凄凉的叫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陆地就在眼前。果然,一片片苇草在微风中不停地摇曳。 我们把船锚在浅滩上,空手爬上海岸。谁也没有勇气去钻苇丛,一致决定回到大船上,等天亮再到这里来。可是到舢板跟前一看,海水已退得干净,小船已像待毙的海兽,歪在泥滩上,7个人又拉又拽,小船纹丝不动。我们只好住在这里了。 七个人卷卧在不足三平方米的舢板内,忍受着饥渴,忍受着焦烁,但是还得彼此安慰。我躺在舢板一角,仰望长空,只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从海面吹来的夜风,掠过水面,掠过芦苇,掠过小舟。在风的摩挲和极度疲倦折磨下,渐渐睡着了。 日出了,大海、苇滩沐浴在霞光里。退潮后的沙滩,浮腾起一片氤氲水汽。夜间所呈现的种种可怕现象,现在看来都那样可笑,远望我们调查队的其他几条船,相距在几公里之外,显然对我们爱莫能助。现在首要任务是寻找石油工人,请他们帮助拉船和解决吃喝问题,同时修理机器,上岸勘察定位位置。 正在钻井的石油工人,听说我们的困难后,立即伸出援助之手,黄河牌大卡车载来一车工人和一些吃的东西。大家用力帮我们抬船,这里的泥滩真怪,竟把船吸得纹丝不动。几十个小伙子却怎么也抬不动这条只有3吨重的小船,从上午一直折腾到中午,白费力气,只好坐等涨潮了。 下午4点钟,潮水慢慢爬到了舢板旁,船开始上浮。就在这时,我们望见远方潮沟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逐波而来,约有3米多长,上面闪动铁青的光芒。开始我们以为是一段木头,并没在意,后来看到一个渔民神色仓皇地向我们跑来,才知道事情有些蹊跷。 原来那段“木头”竟是个活生生的大家伙,它顺着潮水沟,直扑正在沟沿撒网的那位渔民,吓得他将网砸向那个“海怪”,这才逃脱。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后,我们环视下四周蜂拥而来的潮水,惟恐那个怪物尾随而至,每人手中都操起一个家伙,严阵以待。 等惊魂稍定以后,应那个渔民的要求,我们帮助他去寻找丢失的渔网,但是当船驶到那里,怪物和渔网皆渺无踪影。天渐渐黑了,我们把渔民送到安全地带,驶回了大船。 回味着一整天的经历,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黄河口,你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后来一段时间,大家都有一些杯弓蛇影,海上一遇见黑乎乎的东西,就以为是海怪,齐集甲板,严阵以待。最终证明,那只不过是一段烂木头,或一团破渔网而已!(后续) [作者简介]侍茂崇,中国海洋大学教授,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海洋系,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物理海洋学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特邀编辑、中国海洋年鉴编委、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海洋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海洋监测中心顾问和广西科学院顾问,以及海南海洋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和南海海洋调查研究中心总工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山东省“科技兴鲁”金质奖章获得者;多次获得省、部级和国家优秀成果奖。累计公开发表科学论文100余篇,并著有《海洋调查方法》、《海洋调查方法导论》、《物理海洋学》和《物理海洋学导论》、《海洋锋》、《海洋与环境》等专著、译著多部;还著有《海洋史话》、《海洋资源》、《沧海桑田》、《化石鱼追踪记》、《蔚蓝色的涌动》、《海上六十天》、《海洋奥秘》、《海洋动力资源》、《一代宗师---赫崇本》和《冰河演替与海陆沧桑之变》等科普著作十余部,是我国著名的海洋科普作家。 注:该文作者根据早期发表的《浪里也风流》(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年)传记著作手稿,按平台宗旨进行了重新整理与编排,借此深表感谢!故事大标题由平台依据作者提供的全部故事内容另加,并以连载的形式推送,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与认可!故事拟以海洋调查为主线,展现一位海洋人对海洋事业的执着、奉献与人生观,特别是在他身上所呈现的那种求真务实、刻苦钻研、淡泊名利、献身海洋的科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