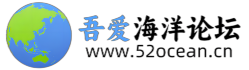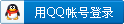我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渔船船旗国,渔船、船员被其他沿海国抓扣的事件频繁发生,作为沿海国,我国也随时面临他国在ITLOS针对我国提起迅速释放之诉的可能,因此,厘清ITLOS的迅速释放程序与国内程序的关系对我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给我国更好地维护海洋权益带来一些启示。
% y" |" v8 \+ m一、作为渔船船旗国的启示
( m. O; S1 k4 w( F2 c4 i/ G1.适当利用迅速释放程序
/ G3 K" G5 A) ~. }6 X: n! x- a" e我国向来秉持不将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国际争端交由第三方机构解决的立场,实践中,外交途径也是我国解决渔船、船员被扣事件的主要方式。例如,2017年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以我国渔船在其管辖海域非法作业为由扣押了我国的渔船及21名渔民,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声明:该渔船是经东帝汶政府批准在相关海域进行作业的,我国通过外交渠道同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当局进行交涉,推动我国渔船、渔民尽快获释。然而,外交途径相对于迅速释放程序而言通常耗时较长,易使我国船员受到长期羁押而遭受损害,且给渔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笔者认为,我国应当结合现实情况适当利用迅速释放程序,将有关争议交由ITLOS审理,主要理由如下:
( w# h4 B' E4 J9 C' W) G! W, k首先,迅速释放程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有利于及时保护我国渔船、船员的利益。如前文所述,迅速释放程序既不适用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也不受沿海国国内未决诉讼和扣留行为是否合法的影响。《公约》第292条要求,法院或法庭应不迟延地处理关于释放的申请,且沿海国在收到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保后,应当迅速遵从释放裁定。实践中,该程序具有极强的高效性和实用性。根据《ITLOS规则》第112条第3、4款的规定,每一当事方仅有1天的时间提交证据及陈述论据,IT-LOS应在收到申请之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起15日内确定听证日期,并在听证会结束后不迟于14日公开宣判。简言之,船旗国向ITLOS提出迅速释放申请后,至多31日即可收到释放与否的决定。在ITLOS目前审理的9个迅速释放案件中,其中6个都判决沿海国迅速释放被扣渔船和船员,有效地解决了沿海国和船旗国之间的争议,使船旗国免遭重大损失。' r6 ~& E7 C+ T1 C7 |. [
其次,迅速释放程序具有一定的私权性质,通常不会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且符合争端解决司法化这一国际趋势。一方面,一个国家是否选择运用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取决于国家对自身实力、对争端解决能力的预期及对利害关系的权衡,主权国家应当在考虑本国利益、争端本身特点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争端解决方式。我国不愿将国际争端交由第三方机构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避免第三方机构的裁决损害我国的国家主权及利益。就我国渔船、船员被扣的纠纷而言,该纠纷不同于其他具有主权性质的国际争端,主要涉及的是船东和船员的私人利益,法律效果也由私人主体承担。反观迅速释放程序,它也不同于一般国际争端解决程序,该程序仅处理释放与否的问题,不涉及其他实质性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争端本身的特征来看,迅速释放程序都是适宜解决渔船、船员被扣纠纷的方式。另一方面,参与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是世界法治化的环境要求,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要求。如今,国际争端的司法化解决已成为一大国际趋势,适当利用迅速释放程序有利于我国顺应这一趋势,缓和我国与扣留国的冲突,高效解决渔船、船员被扣的纠纷。- W! |5 l/ e! }- V6 d' E
最后,ITLOS在迅速释放案件中极易获得管辖权,杜绝迅速释放程序的运用将导致我国与其他沿海国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由前文可知,ITLOS在迅速释放案件中拥有“剩余的强制管辖权”,且《公约》缔约国无权对该程序提出保留。对我国而言,这意味着将渔船、船员被扣的纠纷交由ITLOS审理通常不存在管辖权障碍,利用该程序解决争端富有便捷性、效率性。而且我国随时可能面临他国提起的迅速释放程序,一味否认该程序的运用,易导致我国与其他沿海国在渔业争端解决中处于不对等的劣势地位。* y) @! p8 a" b) @3 d6 Q4 |
2.及时利用迅速释放程序
v! ~3 V- A2 g1 P. p国内程序对迅速释放程序的影响之一体现在,“没收渔船”判决的终局性可能导致迅速释放程序不再具有临时性,迅速释放程序因为失去客体而没有继续进行的必要。2007年7月,日本同时向ITLOS提起2件要求俄罗斯联邦履行迅速释放义务的申请——“富丸号”案和“丰进丸号”案。这两起案件不仅当事国相同,案情也颇为类似。然而由于日本起诉时俄罗斯国内程序处于不同的阶段,ITLOS最终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正如前文所述,在“富丸号”案中,ITLOS认为俄罗斯国内法院已作出了没收渔船的终局判决,它无须再进行迅速释放程序。而在“丰进丸号”案中,日本向ITLOS提起迅速释放申请时,俄罗斯国内程序正在进行之中。最终ITLOS要求俄罗斯联邦应在日本缴纳保证金后迅速释放渔船及船员。正是由于船旗国日本申请迅速释放的时间不同,导致了这两起案件审理结果的差异。这表明在迅速释放程序中,诉讼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船旗国采取的行动是否及时。
( ^+ \! r2 A0 A6 q U1 ^: I6 ]( j; {" f正如ITLOS在“富丸号”案判决中所强调的,船旗国有义务在合理的时间内及时采取行动,才能实现第292条的目标。迅速释放程序作为利益平衡的产物,在保障船旗国利益的同时也包含了相应的限制条件,首要的便是要求船旗国应及时采取救济行动,不应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国作为渔业大国,应当清晰认识到沿海国国内程序终局性对迅速释放程序的影响,在渔船、船员被扣的事件发生后,应在扣留之日起10日内尽快向ITLOS提出迅速释放申请。由于迅速释放程序审理时间较短,只要及时提出申请,在沿海国国内程序终结前通常可以得到迅速释放程序的救济。8 u+ D) |$ c5 {& R$ @0 }# H, E0 d2 w( f# ^
二、作为沿海国的启示, I* y Q7 x& ^# j6 F! t; v
1.制定合理的迅速释放程序应对策略
G7 w, h; }1 {) ]$ y若我国抓扣了他国的渔船、船员,船旗国可能根据《公约》第292条向ITLOS提起迅速释放程序。此时,我国应当正确把握迅速释放程序与我国国内程序的关系,制定符合我国最佳利益的诉讼应对策略,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7 D7 W) ^' l. h4 Z7 p
第一,迅速释放程序具有独立性,其他船旗国可以不经任何国内程序向IT-LOS提出释放渔船、船员的要求,也不受我国扣留行为合法与否的限制。在诉讼中,我国不应以“用尽当地补救办法”“国内诉讼未决”或“扣留行为合法”作为抗辩理由。第二,我国的国内程序具有独立性,对于在我国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捕捞而被抓扣的渔船、船员,我国有权独立审理案件的是非曲直,不受ITLOS为得出结论而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约束。在迅速释放程序中,应当谨防船旗国或ITLOS侵犯我国国内程序的独立性。若ITLOS在诉讼中减损了我国国内程序审理案件实质性内容的权力,可以以违反第292条第3款的规定为由进行抗辩。第三,保证书及其他担保方式决定了我国国内程序的判决能否顺利执行,保证金数额、性质及形式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前文所述,ITLOS在审查保证金的合理性时主要考量的是“所指控罪行的严重性、根据沿海国国内法可能施加的处罚、被扣渔船或货物的价值、沿海国要求的保证金数额及其形式”等要素,这为我国确定保证金具体数额指明了方向。在迅速释放程序中,我国应在考量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船旗国提供的保证金数额,避免ITLOS认定保证金不合理而重新确定担保金额。在担保形式方面,“伏尔加河号”案证实了沿海国仅可设定财政性质的担保方式,ITLOS所作的决定对我国作为沿海国具有启发意义。于我国而言,在释放因违反专属经济区渔业法律法规而被抓扣的渔船、船员时,要注意不应设置非财政性质的担保条件,否则可能面临违反国际义务的后果。
5 V7 B0 w, x' i& A6 r2.完善相关国内法
8 u- w- P/ }7 s由于国内程序将对迅速释放程序产生影响,沿海国的国内法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迅速释放的裁判结果:一方面,“所指控罪行的严重性”和“根据沿海国国内法可能施加的处罚”是ITLOS认定保证书合理性、确定保证金及其他担保方式时的重要考量因素,这两个要素皆以沿海国国内法的规定为基础;另一方面,“没收渔船”是沿海国打击IUU捕捞的有效举措,根据国内法作出符合正当程序的没收终局判决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被扣渔船、船员再次从事非法捕捞。由此可见,我国应当重视国内法在迅速释放程序中发挥的作用。
7 w5 s7 G5 N5 U7 u- ^6 S" ~目前,我国规制外国渔船、船员在专属经济区入渔活动的现行法律主要包括《渔业法》《外国人、外国船舶渔业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渔业法实施细则》《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警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存在法律责任过轻、责任类型及惩戒措施不完善、表述过于原则等缺陷。
) q2 }1 z. B4 P' S201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渔业法修订草案》)正式公布。其中第65条涉及“外国渔业船舶违法入渔处罚”,相较原法的内容明确了从事IUU捕捞活动的外国渔船不得进入我国港口及进入港口的处罚措施;增加了责令返回指定港口、驱逐进入港口的IUU捕捞船舶的规定;大幅提高了罚款额度,将最高罚款金额提升至500万元,并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渔船。《渔业法修订草案》增加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及没收渔船的情形,加大了罚款的处罚力度,符合我国渔业资源管理的实际需要。鉴于国内法在迅速释放程序中的重要性,我国应当尽快以该修订草案为基础通过新的《渔业法》,适用新处罚标准,促使ITLOS依据我国国内法评估保证金的合理性、在确定保证金及其他担保方式时能够有效保障我国的合法权益。
9 R0 B# @+ O+ p: K同时,《渔业法修订草案》第65条仍存在不足之处,可考虑进一步完善。首先,第65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渔业船舶”,但未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容易导致个案认定产生偏差。可以考虑在该条或《渔业法实施细则》中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例如,规定应当考虑非法捕捞渔获物的数量、价值、次数、具体行为等与法益侵害程度相关的要素。鉴于“没收渔船”是打击IUU捕捞最有力的举措,可以考虑适当拓宽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实行力度。尤其是针对通过更换船旗、名称、船员反复实行IUU捕捞的渔船,可以增加在没收后报废处理的规定。其次,第65条仅提到外国渔船、船员从事非法捕捞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删除了《渔业法》第46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第65条中重新纳入外国渔船、船员刑事责任的规定。一方面,重新纳入这些规定具有符合渔业领域法益保护需求、满足刑事立法时效性、加强渔业法与刑法的衔接、增强刑法可预测性等优势,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另一方面,《渔业法》中的这些规定能够增强外国渔船、船员涉渔刑事责任的明确性,在ITLOS考察“违法行为严重性”“根据国内法可能施加的处罚”时得到指引,以避免我国的刑法规范遭到虚置。考虑到原第46条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具有实质意义,还可以选择在《渔业法修订草案》第65条中适用“指引性的立法模式”,即在条文中明确指明可适用的刑法罪名。从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规范来看,外国渔船、船员在我国专属经济区非法入渔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及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故可以在《渔业法修订草案》第65条中增加“以上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第341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的内容。
) H4 Z8 Z- Y6 C/ }) i/ g; i此外,虽然《海警法》没有规定没收船舶的具体情形,但该法第61条规定了经市级海警局以上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海警机构可以先行依法拍卖或者变卖“长期不使用容易导致机械性能下降、价值贬损的”船舶。这一规定补充了《渔业法修订草案》第65条的相关规定,既有利于在沿海国国内程序推进较慢的情形下,更好地维护船旗国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沿海国更好地应对船旗国可能向ITLOS提起的迅速释放之诉。然而,如何判定“长期不使用容易导致机械性能下降、价值贬损的”船舶(包括渔船)尚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建议未来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厘清。# E/ f. m- ]7 q6 i
概言之,我国应当准确把握迅速释放程序与国内程序的关系,善于适当、及时地利用迅速释放程序,同时制定迅速释放之诉应对策略,完善相关国内法,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9 E: P9 s/ t( J- J9 ]: I - b. F$ T* M: N4 ~/ X1 E) ]7 z
文章来源:节选自《国际海洋法法庭迅速释放程序与国内程序的关系探析——兼论对我国的启示》,原刊于《武大国际法评论》2021年第4期# V2 i' V2 X" Y
作者:施余兵,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庄媛,厦门大学法学院硕士
. C, j* m% W/ J$ H
* p( l8 e. |* H4 ]5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