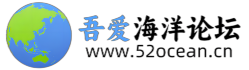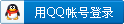|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南极条约》缔约国不仅加大了在南极条约区域科学考察的频率和强度,而且还正在尝试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甚至,还有诸多游客与非政府组织也接踵而至。为了避免脆弱的南极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于1991年达成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又称《马德里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作为《南极条约》的补充文件,该《议定书》于1998年1月生效,提高了参与南极事务的门槛,成为迄今唯一保护南极环境但仅对《南极条约》缔约国开放的多边条约。
) k) @& u+ y" ?4 X7 T, J- g《议定书》将南极条约区域指定为自然保护区,要求在该区域内的所有活动均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减少、防止对南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如果在南极区域活动中因《议定书》的解释或适用而发生争端,当事方除了运用协商、调解、协调等外交法外,还可以通过书面声明选择仲裁方法或者国际法院方法来解决争端。从《议定书》及其附件本身看,仲裁方法可谓相当凸显。但鉴于南极条约体系的独立性,加之缔约国在南极地区活动的环境影响趋势以及南极环境的脆弱性,从国际法角度,明晰解决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争端之仲裁方法的地位和性质,澄清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及其例外,探讨仲裁庭可适用的法律及有关辅助资料,剖析仲裁裁决执行中的某些难题,对促进和提高仲裁方法的实际效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期望能及时完善有关内容,使环境仲裁成为南极条约体系下自足独立且具有权威性的完备程序。 7 g( \: v& x6 e
一、仲裁方法在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争端解决中的地位与性质 % h( x6 o# R0 T/ S- i
为了促进对南极环境以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根据《议定书》,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之下设立由各协商方代表组成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全面负责《议定书》的适用和实施。协商会议还根据《南极条约》,单独或集体安排环境监督员进行环境监察,涉及南极所有考察站、装备、设备、船只和飞机。就当前南极区域的吸引力看,环境监察的事项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 N5 r: b" R3 ^& S" O6 o" ^基于环境监察的事实和结论,环境责任及由此引发的争端便会跃然纸上。按照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以及《议定书》的要求,争端当事方应尽可能快地在其间通过谈判、调解、调停、仲裁、国际法院等和平方法解决当下争端。就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而言,“仲裁和国际法院是迄今被环境条约起草人最广泛借助的法律方法,几乎所有环境条约下的争端解决都包含这两种方法。” / F9 S r( M; T( V) i; e% H
与仲裁方法相比,尽管在费用支出上国际法院方法占有优势,但该机构有繁重的工作负荷。仅就诉讼管辖权来看,截至2017年3月31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有72个国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项向秘书长交存了承认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声明,另外还有300多个双边或多边条约包含解决此类条约的适用或解释所引起的争端可诉诸国际法院的条款。此外,联合国会员国也可根据特别协定向国际法院提交具体争端。而国际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半数以上是领土和边界纠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环境事务发展的关注和重视,国际法院曾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26条第1款于1993年创建了环境事务分庭,且断断续续重组了13年(至2006年),但从未受理过任何环境案件。而且,就目前情况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通过递交书面声明,接受或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5 P4 ^1 {4 A8 R3 k/ f
一般情况下,仲裁是争端当事方一致同意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它是以自愿管辖为基础,裁决结果对当事方有拘束力。当事方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就意味着“诚心遵从裁决的义务”,即自愿承担履行裁决结果的义务。由于国家主权的作用,“自愿协商一致”应该是争端当事方援用仲裁方法的逻辑起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仲裁可以被看做是包含调停和调解方法在内的准外交程序。从整体上看,仲裁裁决更能让争端当事方满意,仲裁裁决的执行情况也远远好于国际法院的判决结果。但由于南极在国际法上的独特地位,《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规定将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争端解决的仲裁方法渐次引申为争端当事方必然选择的方法,甚至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
0 }- M0 v2 E" y其一,作为争端当事方一致明示选择的方法。这种情况用于禁止矿产资源活动、环境影响评估以及紧急反应行动等引发的环境争端。矿产资源活动可对环境造成大规模损害,而且常常难以恢复原状,因而《南极条约》和《议定书》均对此作了禁止性规定,要求任何国家都不得在南极条约区域从事此类活动,否则将引起环境争端。环境影响评估一般是南极环境委员会或南极环境监督员通过对某缔约国南极活动的数据资料分析而得出其对环境有害或无害影响的情况,如果评估结果为有害影响,就会涉及环境责任问题,因而也会发生争端。紧急反应行动则是其他缔约国对一缔约国(包括国家运营者和非国家运营者)的南极活动所引发的紧急环境情势而采取的救助措施,但如果产生的救助费用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补偿,即会引发环境争端。在此类情形下,任何一方提出请求且争端当事方一致同意,即可援用仲裁方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种明示选择不仅能满足争端当事方的主权意志,更成为争端当事方权衡国际法院和仲裁等法律方法之后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要考量司法经济和政治成本。
- C1 R* Y1 r6 N. c其二,作为争端当事方未加声明而推定选择的方法。国际环境条约一般都不允许保留,而且缔约国在环境条约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远大于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在加入之时往往会更加谨慎地对待环境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而《议定书》则要求,如果争端当事方的一方在加入时未在援用仲裁和国际法院两种方法上做出书面声明或者声明的有效期已过,则应被视为接受仲裁庭的职能。这显然是对争端当事方在争端解决方法选择上出现空白时进行推定的结果,是一种强制性的填充。而且,即便《议定书》的缔约国递交一份新的声明、撤销通知或者延期声明,均不应在任何方面影响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
4 W% \- `! }$ g f- [2 o4 q) f2 J其三,作为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为争端当事方指定的方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争端当事方均能就争端解决方法达成一致意见。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但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以便及时保护脆弱的南极环境,如果当事方接受的解决争端的方法不一致,争端只能提交仲裁。尽管《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规则文本中没有“指定”一词,但争端当事方如果在享有选择争端解决方法权利的同时不能达成一致选择,它们的这种权利即可被剥夺,这也可看做是解决南极环境争端“兜底”的强制性方法。
) u$ F, q/ v3 V0 U其四,作为排除援用国际法院之后的方法。从主权角度看,缔约国就所涉争端的解决既可以选择国际法院,也可以选择仲裁,但也不排除同时选择这两种方法的可能性。但根据《议定书》,在南极环境争端中,如果争端当事方同时选择了仲裁和国际法院两种方法,那么争端只能提交仲裁。这一规定不是一个任意选择题,而是剥夺了争端当事方在国际法院和仲裁之间二选其一的选择权,有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即:将争端当事方选择援用国际法院的方法被排除在外,由此大大增强了仲裁方法的强制性选择地位。 + ?: C7 x2 F8 C( i
二、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及其例外 ! U+ t Q2 K4 T+ u! X1 P* |
仲裁庭有权解释并裁定其对当前提交的争端是否有管辖权。但仲裁庭在做出裁决之前,应确保其就当下争端的职权以及提出的诉求和反诉建立在良好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并“禁足”其不能管辖的环境争端事项。
8 d, t! A" [: n) B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 A- ?4 m/ y6 q/ ^8 Z& b根据《议定书》及其附件,应争端当事方请求并根据仲裁时间表建立起来的仲裁庭,有权解释并裁定其对当前提交的关于共识环境事项、环境紧急事项以及环境紧急情势引起的经济补偿等争端是否有管辖权。
/ }8 b# z0 X9 [5 V! L) j首先,共识环境事项争端是指《议定书》缔约国之间在南极环境保护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并承诺接受《议定书》及其附件严格约束的那些事项上的争端,重点包括南极矿产资源管理和环境影响评估两个方面。对矿产资源活动给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国际社会已早有共识,因而《议定书》要求,与矿产资源有关的任何活动,如果不是科学研究,则应予禁止,直至达成相关的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应充分保障所有及于《南极条约》禁止主权和主权权利诉求以及使用相关原则的所有国家的利益。对于与南极矿产资源有关条款的修订,于2048年之前,应由南极条约协商方审议大会讨论有关方案,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决定。
% l+ J# y0 S; f环境影响评估可以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工具。为确保任何活动不给南极地区带来显著的或潜在的影响,在批准或拒绝任何南极活动或项目申请之前,均应给予充分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充分体现了“有害原则”与“合作义务原则”,且已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义务。3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91年通过的《跨界情形下的环境影响评估公约》,评估需要考虑拟进行的项目对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健康的影响。但由于南极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性,环境影响评估则用于人类活动(包括拟进行的项目)对南极环境尤其是对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凡在南极条约区域进行包括科研、旅游、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运输支持活动等可能带来些微影响或暂时影响的,均应做事先评估,包括初始环境评估和综合环境评估。前者用于此类活动对南极条约区域环境有些微或短暂影响(a minor or transitory impact)的活动的评估,后者用于评估可能对南极条约区域环境带来多于些微或短暂影响(more than a minor ortransitory impact)的活动。“尽管决定一项活动应否首先进行初始环境评估还是综合环境评估的重点是对‘些微或短暂影响’的概念辨析或释义,但在这个术语上,南极条约协商方至今还未达成一致,而确定‘些微或短暂影响’的困难似乎就在于与每一活动有关的各种变量与每一环境状况之间的依存关系。”
~" [% T4 C" }7 T其次,环境紧急事项争端是指因发生的任何意外对南极环境造成或即将威胁造成任何重 : d6 U, @ i y
要有害影响的事项而引发的争端。对于环境紧急事项,争端当事方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另一方或多方以及秘书处,请求建立仲裁庭。在仲裁庭确定其管辖权的初步证据之后,就可以为因紧急情势而发生环境争端的任何一方指定或者说明应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指定的临时性措施”是指发生环境紧急情势后,仲裁庭认为有必要维护一争端当事方的相关权利而明确指定另一方应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说明的临时性措施”则是指为了防止环境紧急事项对南极环境或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向争端当事方说明应采取的任何适当的临时性措施。前者具有临时裁决的性质,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后者是引导性的提示说明,需要争端当事方的自觉行动。 9 d( o4 S* K+ k
最后,环境紧急事项引起的经济补偿争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国家行为者(state actor)对紧急状态下的环境保护没有采取立即有效的反应行动,即应承担补偿其他缔约国采取此种行动而产生的费用;二是如果一国家行为者没有采取立即有效的应对行动,其他缔约国也没有采取应对行动,则该国就应支付南极条约秘书处基金会(以下称“基金会”)采取应对行动而产生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仲裁庭解决此类争端是在践行环境法上的“谁污染谁支付”原则。任何为紧急情况的环境保护所付出的,都应该得到几乎同等水平或数量的补偿。由于补偿是一种经济行为,且由于基金会目前筹措资金尚存在困难,这里还需要被裁定“败诉”的一方能积极配合而“不赖账”,也就是下文要讨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 , y! h: @0 ~) p0 @1 i0 N
仲裁庭管辖范围的例外
2 F3 N) r: C: b3 X. y( k% {5 P一是仲裁庭不应受理与海上安全事项有关的争端。具体而言,因船体安全和海上救助生命不得已造成石油排放、有毒液体物质排放、垃圾排放以及污水排放而引发的环境争端,因保护人的生命或安全的行动或疏漏、未能遇见且不可预防的南极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以及针对行动者活动的交战行为而引起的环境争端,均不在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海上安全事故或事件皆由不可抗力造成,但缔约国在意外发生时应采取减少污染的应急措施,尤其是针对石油船舶;同时,还应与国际海事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交流意见,解决当前遇到的环境污染。 ' e! m( q' W1 O& m w Z
二是仲裁庭不应受理国家主权豁免事项的争端。在南极条约区域,缔约国应考虑保护南极环境的重要性,但不禁止任何国家在遵守、尊重南极条约体系基础上行使合理正当的主权行为。根据《议定书》及其附件,对用于和平目的或者科学研究目的的军事船舶、海军设备以及其他与国家使用和拥有的船舶有关的活动带来的环境问题,仲裁庭因受国家主权豁免的限制而不能对此类争端行使管辖权。而且,由于国家主权豁免,凡与此有关的争端,也不适用《议定书》规定的争端解决的其他方法。
5 @4 v; Q6 |8 W1 `$ X# e+ t: L三是仲裁庭不应受理与南极领土主权及主权权利有关的争端。根据《南极条约》,任何国家都不得对南极条约区域提出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和诉求;在《南极条约》的有效期内,发生的任何行为或行动都不应作为主张、支持或者否定南极领土主权要求的基础,也不创设任何南极主权权利,不得提出南极领土的新要求或者扩大既有要求。为了支持《南极条约》的这些原则性规定,环境仲裁庭当然就不应决定或者裁定与南极主权和主权权利有关的任何事项,也不应通过解释《议定书》及其附件的任何条款来决定或者裁定与南极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有关的任何事项。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南极条约缔约国通过加入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向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提出了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方案并正在付诸实践。因此,关于保护区与南极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恐怕也是南极环境仲裁庭应该高度警惕的问题。
9 S2 T# T1 V% Z. j三、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庭可适用的法律及其辅助资料
1 ?! q+ e8 L2 K3 @8 ? @, l' a在南极环境争端解决中,尽管仲裁以“自愿协商一致”为起点,但《议定书》及其附件未载明争端当事方可在仲裁协议中写入双方选定的由仲裁庭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而是要求仲裁庭“应根据《议定书》条款及其他与此类条款相一致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裁决争端事项;仲裁庭经争端当事方同意,可适用‘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决争端事项”。由此可以推定,仲裁庭适用法律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e generali)的原则。可适用的法律往往对裁决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这里需要澄清特殊法和一般法的范围及相应的辅助资料。 9 D* ]# ~8 B3 T% U. \9 g
仲裁庭应适用的特殊法是指《议定书》及其附件,但也不可忽视与此有关的谈判记载资料的辅助作用。这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其一,《议定书》是用于保护南极环境的专门性法律文件,仲裁庭不仅应遵循《议定书》的宗旨、原则和规则,还应依照与此有关的6个附件的规定来审理当前的争端事项和问题。其二,从《议定书》的全称看,它是对《南极条约》下“维护和保护南极生物资源”规定的具体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南极条约》可视为《议定书》的“母约”。“维护和保护南极生物资源”的规定,最初用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进一步交流环境信息,要求各协商方从南极的共同利益出发,向政府提出、推荐或者考虑《南极条约》目标和原则下的事项。尽管它是在1959年达成的比较笼统的规定,尽管近30年之后才有生效的《议定书》,但南极条约协商方关于南极环境保护的协商记录以及《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谈判记录,均可以作为仲裁庭适用的法律的“辅助资料”,或可从中寻找达成《议定书》及其附件之时对南极环保议题或事项的理解或释义。谈判记载资料作为国际司法机构裁决案件的辅助资料已司空见惯,国际法院、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等都有过此类实践。 % s7 K3 H. z$ q3 a( V
仲裁庭应适用的一般法是指其他与《议定书》有关条款相一致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宽泛且不太好确定的问题。而且,将国际法原则用于争端解决,确有一定的难度。国际法原则作为“不确定内容的规则”显得比较抽象,尽管不可能从不确定的内容中推导出清晰的法律义务,但它(们)确实是对国际法主体施加必须遵循的某种(些)义务。而国际法规则大多都能清晰反映国际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南极环境问题看,此类原则和规则实际上已经囊括在《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其6个附件当中,是南极条约协商方“既有作品”的重现,重点包括1964年《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72年《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以及1988年《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等。此外,南极环保事项也与其他国际条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在保护南极动植物问题上,对于“与南极条约体系之外其他协定之间的关系”,仲裁庭应“不减损缔约国在《1946年捕鲸国际公约》之下的权利”;在防止海洋污染方面,仲裁庭还应考虑《1973年禁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其《1978年议定书》。
2 Y" Y$ W- s! m8 G4 I此外,由于“公允及善良原则”是世界各主要文明代表国家和各大法系代表国家国内法特别是司法中所存在的一般性、共同性的法律原则,不仅见于《国际法院规约》和《仲裁程序示范规则》,也见于《议定书》的附件《仲裁安排》中。作为非法律标准的适用时,该原则意味着仲裁庭在严格适用《议定书》及其附件规定将会发生不公平的裁判结果且在争端当事方同意并明示授权下,仲裁庭不再严格适用条约的规定,而是依据争端的具体情况,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且要在不违反南极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的范围内,依据仲裁庭所承认的“公允及善良”来裁定当事方之间的争端。
( Z$ |: {, r5 [3 X) B' _( r实践中,国际司法机构通常会引用既有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辅助资料来审理当前案件,或者说它们“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对于司法判例,南极环境仲裁庭可根据既成案件对具体争议问题的解释或者法律适用情况来决定其对当前案件的作用,比如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在1973年“核试验案”中,新西兰援用了“禁止污染人类环境”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国际法院因此给予其关于环境保全的举证机会。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暗示。尽管该案因法国单方面宣告停止核试验而终止,尽管1958年《公海公约》已有提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环境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已经形成了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一般原则,即:它们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保护和改善这些地区的环境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项。 # C$ H' t' ?! p" A/ S
对“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的引用,已有国际司法机构突破这一范围的实践。尤为典型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美国诉中国稀土案”中不是引用“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而是援引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作品中的观点,或可称之为“权威最高之经济学家学说”,以此作为一项依据来推理中国稀土限制措施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如果说裁决国际贸易争端案件可以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话,那么在解决南极环境争端上,仲裁庭除了可以引用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之外,似乎也可援引与南极自然地理特点相关的其他学科专业领域的学说或数据,作为裁定案件的依据。
) V2 n( `: h) g0 {" V四、南极条约区域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难题 . R% a+ a% Y; A) ~, i
仲裁裁决通常是一次性的,争端当事方在选择适用仲裁方法时通常都已约定遵守或执行仲裁裁决。联合国1958年《仲裁程序示范规则》就要求:“裁决应构成争端的确定解决”,“裁决一旦做出,应对当事双方有拘束力”。当然,一般也都不排斥对仲裁裁决的修正或解释。只是在实践中,这种修正或解释裁决书内容的情况,容易引起更多的争议。“1989年塞内加尔诉几内亚比绍仲裁”案中,因仲裁庭长在裁决中的附加说明,就引发了双方关于海域划界的进一步争议。
4 X& Y; F( g. s) s9 a( w4 P南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本质上也是环境责任的承担问题。这里的环境责任,应该与《议定书》保护南极环境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生态环境目标相一致。为此,缔约国应遵循《议定书》关于环境紧急情势责任的详细规则和程序。但这些规则和程序是什么?这显然是《议定书》生效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于是,《环境紧急事项引起的责任》(以下简称《紧急责任附件》)这一新的附件于2005年诞生了。
g$ I B; F# A$ A. e, Q( f从这一附件看,南极环境责任的承担问题基本上遵循国际环境法上“谁污染谁支付”的原则。但是,由于南极环境责任问题是从《南极条约》到《议定书》再到《紧急责任附件》的更为具体的法律化过程,仲裁庭在适用“下位法”时,不得不考虑“上位法”的根本性影响;又由于环境责任与南极区域的科学研究、旅游及其他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关,仲裁庭也不得不考虑裁决结果面临的执行难题及其可能带来的进次环境责任纠纷。 ( {6 `- X. G" v, S+ y
其一,国家主权豁免是否就意味着环境责任的免除?国家主权豁免是由“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罗马法概念引申而来的。根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国家”是指:国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关;有权行使主权权力并以该身份行事的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国家政治区分单位;国家机构、部门或其他实体,但须它们有权行使并且实际在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力;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国家代表。南极地区是致力于和平目的和科学用途的自然保护区,《南极条约》不禁止缔约国为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和平目的的人员和军事装备进入南极区域,而“所有政府组织的活动”在大多数时候都可归入国家主权行为,即:国家在公法上的主权行为,而非司法上的事务权行为。如果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序言中确认“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为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那么因“所有政府组织的活动”而产生的环境责任在法律上很可能就会自动消弭。而一旦开启缔约国“国家主权豁免”作为免责依据的先例,就极有可能对今后仲裁程序的援用和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负面影响。质言之,在现有的南极条约体系下,国家主权豁免或可成为当事国拒绝执行南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最后理由。
/ a8 Q/ @# }1 `5 F3 J! m其二,缔约国的公海权利和环境责任何者优先?《南极条约》适用于南纬60度以南地区,包括所有冰盖,但不应侵害或影响任何国家在国际法上与公海区域有关的权利及其行使。在国际法范围内,国家在公海的权利大致包括公海四大自由以及公海底土(一般为国际海底区域)的有关权利。但《南极条约》是制订《紧急责任附件》的重要渊源,那么在法理上是该偏重于环境责任的地域范围还是该优先考虑运营者在公海的权利?对于这一问题,仲裁庭给出的答案很可能与运营者的诉求不一致,运营者或可以不应损害或影响其享有公海的权利而拒绝执行仲裁裁决。 + M$ s. Y# R/ J) B; n; Z
其三,如何执行应对环境紧急情势后的经济补偿?虽然目前未有过南极环境仲裁案例,但在《紧急责任附件》未来生效后,追究引起环境紧急情势的运营者的经济补偿责任,恐怕不那么容易。如前文所述,这里的“环境紧急情势”是指与在南极条约区域内的科学研究计划、旅游及其他所有政府或非政府活动有关的任何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对南极环境产生或威胁产生重要的和有害的影响。在环境紧急情势问题上,《紧急责任附件》的起草者们可能考虑到极地环境的脆弱性、极地环境保护的科学难题等,要求其他缔约国为环境紧急情势制造者(包括国家运营者和非国家运营者)提供应急援助,由此发生的费用应由环境紧急情势制造者首先提供给基金会,然后由基金会补偿给采取反应行动的缔约国。然而,《紧急责任附件》把对非国家行为者的追责赔偿或补偿的管辖权赋予其经营所在地国、主营业务所在地国或惯常居住地国的国内法院,由此将南极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延伸至国内法院,这显然会加重仲裁裁决执行情况的复杂性。 ( v2 A2 z/ g9 X, p. R# J5 v
从南极地区现有的法律文件看,环境仲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自足的争端解决方法。但如果以上问题不能解决,仲裁裁决的效力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关于环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不仅应该成为今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或环境大会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似乎也应该成为《议定书》未来的又一个附件,由此构成可自足独立完成的且具有权威性的南极环境仲裁程序体系。
8 v! p ?7 x# E+ [5 h: g& z五、结语 - S( \( f+ I+ `
如今,关注和保护南极环境已成为所有国家在南极条约区域开展所有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以往的诸多环境问题可以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及南极环境大会上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讨论或解决,但从南极条约体系的独立性及当前缔约国在南极地区活动的环境影响看,从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及环境污染后的恢复难度看,南极条约协商方达成的强制性的仲裁方法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也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 - q, I7 ?9 |% X$ z4 A
南极条约区域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致力于和平目的和科学用途的自然保护区,援用仲裁方法解决南极环境争端显然应该与此保持一致。尽管仲裁方法一般都具有封闭、保密的性质,但“南极环境争端”一词本身就包含高标准、高道德的要求,也会对仲裁庭潜在地提出高水平和高效用的要求。在确定其管辖权的同时,仲裁庭应该谨记那些不应该涉足的事项,尤其不应涉足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之争,同时更需要考虑国家主权豁免及其对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在确定可适用的法律方面,仲裁庭应明晰特殊法与一般法的范围及其间的关系,还应特别注意司法判例与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对审理当前案件的辅助作用,但应谨慎对待拟突破此类范围的情形。从现有的南极条约体系看,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约束力,尚需对争端当事方不执行裁决的情形尤其是不执行因紧急情势而发生环境责任的情形提供相应的补救措施,进而从整体上保证南极环境仲裁方法的自给自足与独立有效。
. E0 [. j! t1 `这里还须要指出的是,我国较早加入了《南极条约》和《议定书》,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其他南极条约协商方相比,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南极立法。从我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角度看,推进我国南极立法不仅能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将有助于在未来可能的南极环境争端中有法可依。在南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虽已制定了有关政策,但从适用范围以及当前南极环境的发展趋势看,还存在诸多需要升级和完善之处,尤其是南极环境争端问题。根据前文分析,对于南极环境争端解决,我国无疑应高度重视并能充分援用外交或政治方法,务必高度重视法律方法中仲裁规则的设计。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我国尚未承认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不可能援用《议定书》所指的国际法院方法。另就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看,由于其较为隆重而繁琐的程序,加之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法律地位和国际政治影响力,也不可能就南极环境争端事项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其二,我国尚未批准《议定书》附件六,因而在仲裁方法中必须考虑对于环境紧急情势的责任裁定的难题,防止根据《议定书》及其附件(包括《仲裁安排》)带来的某些纰漏,由此伤及我国有关法律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如今,在我国批准《议定书》二十年后,为了更好地履行南极环境保护的义务,有效保障南极条约体系的自足稳定,切实维护我国在南极地区的权利和利益,增强我国对南极政治和法律进程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我国应推进南极立法并应全面考虑、统筹设计关于南极环境争端解决的仲裁规则。 5 [2 t( {. w- i! U2 y# s0 f ?* G6 a0 H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8年5月 第26卷 第5期
# Q, V- k& W: \作者:李雪平(1969—),女,河南洛阳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本理论、WTO 法、极地法。
) \3 d3 [9 g3 @8 E; {5 j2 b" O5 @6 A. w7 F' f, B2 S
|